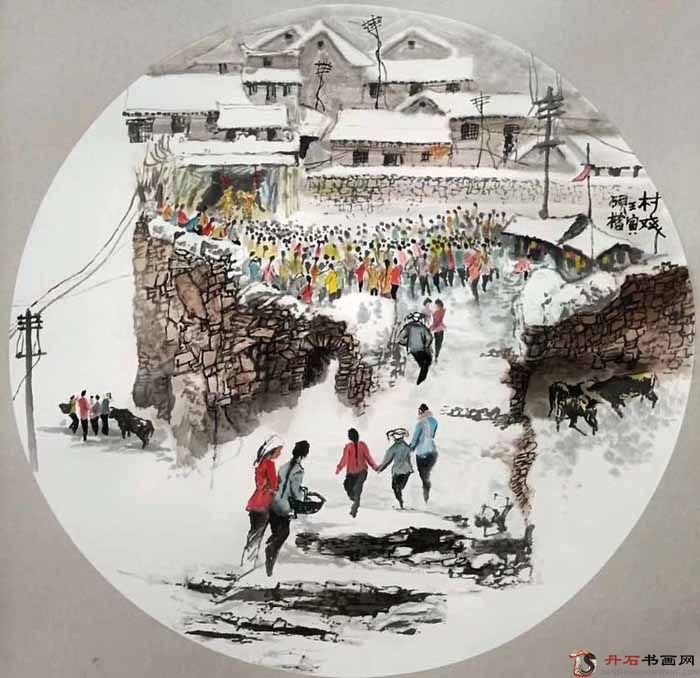诗意山居之【静夜思】
文/砚楷画/砚楷
夜的山中,峰际朗月窥于松枝间,惊鸣栖鸟,如银的水光溢进幽居,映得地面霜白一片,给了夜色一片纯清的美好,竟让人不忍睡去。月亮清照银辉的光紧紧的跟着我的影子行走,若生命在黑夜穿梭中看到天地交替的浓照缩影。

夜风爽且凉,与树的弹拨和上了水声,山月披着圣洁的白裳,触目惊心的斑驳如梦一般隐溢着无言的沧伤。我与月对坐默默,不说话,彼此怜悯着却无法伸手触及。这一刻,没有虚张声势,只有灵魂的安宁,心境更加得淡然自适,触摸一弯月的冷暖,发酵的时间植入身体,将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
与月相视着进入那茫然不着边际的寂静里。煮上一壶茶,独坐月下,什么也不想,只听风声和虫语,心很快也染上了一层绿色,泛起柔柔的薄凉。
却掉了白天太多的修饰,渲染,月夜的山居,只剩下纯净的黑白两色,夜,是真的黑,若水墨的底色,那一抹远山的晕染让我感知背后的意境,没有一丝隔阂。黑是一种底色,密之极则为黑,是玄妙的存在。渐近渐远黑色浓淡,展现出进深感、质感和韵味。与白的月彼此映衬,相得益彰,就如太极图中的阴阳,黑白交融,美的两全。

黑白,是最感性最具生命力的色彩,两者组合成简单而永恒的存在。简约,直白,随性。淡则雅,故是其心。韵则是其质,清水洗心,以求真纯。黑白、日夜,阴阳,黑白一体,黑即是白,白即是黑,黑白同色,繁与简、实与虚等两极元素,花开淡墨痕迹浅,而清气长留。白,是一切颜色之始。黑,则为一切颜色之结。万般色彩黑白始,其间无穷的变幻,即是一个多彩的世界,这才是自然的真实。

美的追寻始自白,疏之极则白,白之虚象可纳万境,白则虚,故心所想皆为景,就像今夜的山月,诱惑我质朴的思绪浸在水色光阴里,暗香从矮墙的风雅中移影而出,不染尘泥。
此刻,整座山沐浴月下,属于我一个人。寂静中,聆听大山微微的鼻息。月照下的山影,清幽且朦胧,岩石与树木的黑影,震慑且肃穆,夜色深处的几声犬吠使得夜月的山居愈加寂静。

静是一种禅意。
刹那的忘我,即美学上“静照”。心无挂碍,和世务暂时绝缘。静观万象,万象如在镜中,光明莹洁,而各得其所,呈现着各自内在的、自由的生命。美感的产生在于空,中国画讲"留白‘’留白即空,对物象造成距离,使自己不沾不滞,物象得以孤立绝缘,自成境界:雾里看花,水中望月,都是在距离化、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幻美。

不论是隔帘看月,还是隔水看花!都是一个“隔”字产生的美感。而剖掉物理条件的心灵的‘空"才是艺术的本源。’司空图《诗品》里形容艺术的心灵当如“空潭泻春,古镜照神”,形容艺术人格为“落花无言,人淡如菊”,“神出古异,淡不可收”。艺术的造诣当“遇之匪深,即之愈稀”,“遇之自天,泠然希音”。精神的淡泊,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:
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
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
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
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
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

然而,静却不是空,乃是由此获得“充实”,由“心远”接近到的“真意”。
"山月皎如烛,风霜时动竹。夜半鸟惊栖,窗间人独宿‘’。是空吗?有月的山中,并不宁静,风在树与树之间穿梭,时而浅唱,时而低吟,如一支柔美的歌。除了风声,隔山的溪瀑只闻其声。不知名的鸟儿此时也被山月惊醒,,此起彼应地互相唱和。树枝断裂和植物拔节的声音,小虫的唧唧,与草丛中不明原委的簌簌……这种种的声音合成了一种“山籁”。

有月照我的山是充盈的,黑暗深处,花蕾轮廓清晰,鸟鸣低下来,一些细小的事物折射山月下偷偷抖落尘埃,牵牛花爬上向日葵的花蕊,在起伏的径上纠缠,秋风满架的黄瓜豆角在夜的缺口上呼吸,月季触及黝黑的光芒,一地月光,风一吹,一晃一晃的,高远的天空愈加高远了。
顺着月光,我们不防找一找去年的桃花。